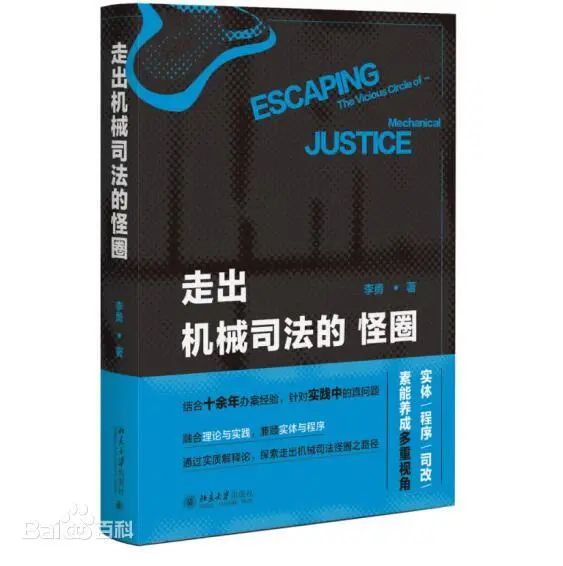李勇:如何运用体系解释方法避免机械司法
作者:李勇
来源:节选自《走出机械司法的怪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一)体系解释的基本内涵
体系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是指根据法条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阐述该法条含义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的哲学根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部分是整体的部分,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不通观法律整体,仅根据其提示的一部分所作出的判断或解释,是不正当的”。[1]作为部分的法条只有放在作为整体的法律之中,才能揭示其准确含义,需要瞻前顾后,充分考虑法条之间的相互关系。“使法律之间相协调的解释是最好的解释”,如果一种解释方法对某一个案件得出一个结论后,会导致这个被解释的条文与刑法中其他相关条文形成重大矛盾和不协调,或者导致分则与总则之间出现重大矛盾,或者导致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出现重大矛盾,那就要反思这种解释结论是否妥当。
(二)体系解释的运用
1.总则与分则的协调
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属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总则对分则具有统领作用。解释分则条文的时候,不仅不得与总则相冲突,而且要以总则为指导。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191条的洗钱罪进行了修改,删除原来条文中的“明知”“协助”“提供”,这样修改的目的就是将“自洗钱”(本犯)入刑,因为对于犯罪分子本人而言,自己洗钱就不存在不明知的问题,也不存在自己协助自己、自己为自己提供帮助的问题。因此,修正后的条文应当理解为洗钱包括:自洗钱(本犯)和他洗钱(下游犯),删除“明知”并不意味着“他洗钱”就不需要行为人明知了。洗钱罪是故意犯罪,既然是故意犯罪,根据刑法总则第14条的规定,当然需要“明知”,刑法总则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如果将分则第191条的洗钱罪解释了不需要对构成要件事实的明知,就必然导致与刑法总则第14条产生重大矛盾。再比如,三次到他人菜地里割三把韭菜的行为,三次到他人果树上摘了三个苹果,三次盗窃三盆“多肉”、入户盗窃两个鸡蛋,将类似这样的行为解释为刑法分则第264条的“多次盗窃”“入户盗窃”,这样的机械套用分则条文,没有与刑法总则第13条对犯罪概念特征的规定相协调。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犯罪必须具有刑事违法性、法益侵害性(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并且还用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以刑法总则第13条作为指导来解释上述行为均没有侵害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不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
2.法律与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解释,而不是对法律的修改。司法解释不得与法律相冲突,对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仍然要以法律的基本规定为指导。例如,大量的司法解释将故意犯罪中的“明知”解释为知道和应当知道。解释刑法的规定,这里的“应当知道”指的是“明知可能”,也是一种可推定的明知,但是不能将这里的“应当明知”理解为“应当预见”,因为根据刑法第15条的规定,“应当预见”是过失犯罪的认识因素。再比如下面这个案例:
[案例]行为人甲女知道乙女与甲的丈夫有不正当关系,也知道乙女平时开的汽车是甲女之丈夫送给乙女的,行为人甲在该汽车上按照定位监控装置,该装置没半小时发送5条位置信息,截至案发时共计发送了150余条位置信息。行为人甲获得这些信息没有出售或用于其他事项,为了保存其丈夫过错的证据,防止未来离婚时财产分割吃亏。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位置信息属于行踪轨迹息,非法获取50条以上行踪轨迹信息属于刑法第253条之一的“情节严重”,构成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机械、孤立地看该司法解释,甲女的行为似乎符合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把该司法解释与刑法第253条之一结合起来看,这样的解释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数据犯罪,犯罪对象是“公民个人信息”,且只有达到“情节严重”才需要动用刑法。这里的“个人信息”显然不是“一个人的信息”,这里的“情节严重”显然不是“一个人的信息被反复侵害了50次以上”。上述案例中,实际上只有一个人的位置信息被侵害,没有达到需要动用刑法的程度,属于违法行为但不是犯罪行为。
3.法秩序统一原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以法的安定性为核心,强调不同法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当在任何一个法律领域中得到许可的一种举止行为, 仍然要受到刑事惩罚时, 那将会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价值矛盾, 并且也将违背刑法作为社会政策的最后手段的这种辅助性。”[2]特别是在行政犯领域,往往以违反行政法为前提,如果行政法规对某种行为都不予处罚,那刑法就不可能得出构成犯罪的结论。比如下面这个案例:
[案例] 2004年,被告人张某强与他人合伙成立个体企业某龙骨厂,张某强负责生产经营活动。因某龙骨厂系小规模纳税人,无法为购货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张某强遂以他人开办的鑫源公司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同。2006年至2007年间,张某强先后与六家公司签订轻钢龙骨销售合同,购货单位均将货款汇入鑫源公司账户,鑫源公司并为上述六家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53张,价税合计4457701.36元,税额647700.18元。基于以上事实,某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某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张某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张某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张某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检察院未抗诉。某州市人民法院依法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张某强以其他单位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同,由该单位收取货款、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其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某州市人民法院认定张某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适用法律错误。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并撤销某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该案经某州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依法宣告张某强无罪。
事实上,这种行为甚至都不违反税收的行政法规,更不可能构成犯罪,2014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已经将这种行为排除在违法行为之外。
- 上一条: 论合伙财产份额的转让 ——《民法典》第974条解析 2024-08-09
- 下一条: 党建军、杨立新:死刑案件适用补强证据规则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2024-08-14
- 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中的体系解释 2023-06-14
- 付立庆:刑法解释的方法和边界 2024-08-01
-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10集)【第1195号】张传勇贩卖毒品案——对以非接触方式交易毒品且被告人拒不供认的案件,如何综合运用间接证据定案 2017-12-22
- 债务加入与保证的性质区分与司法识别丨案例精选 2024-11-26
- 合同争议条款的解释规则与司法认定 2024-10-28